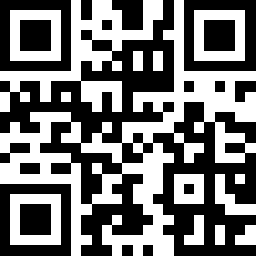24-05-4 21:47 发布于 北京 来自 微博网页版
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现代化也不是发生在真空中或书本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既根植于其历史经验、文明传统和国情特点,又深刻受到现代化发生发展之时的国际体系特征——诸如国际权力格局、意识形态格局与技术格局——的塑造。
相对于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国家建构等层面相对落后,在经济分工上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在政治上处于争取独立自主、摆脱西方控制与干涉的斗争状态,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处于相对弱势和非主流地位。这使得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是争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相对自主、独立和安全地位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和科技问题,而且是安全和稳定问题。
具体而言,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面临更大的外部安全压力:
其一,非西方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威胁。历史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受迫的:正是为了回应和反抗西方列强的威胁、霸凌与侵略,非西方国家才开始建立现代化政治组织与社会汲取动员体系,实行各项改革,走向现代化道路。而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步后,西方列强甚至会变本加厉,试图将潜在的赶超者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二,非西方国家的政权安全时刻面临严峻的意识形态渗透压力。二战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国际体系的规范规则为之一新,西方列强无法像从前那样随意吞并、肢解和奴役一个主权国家。但西方列强转而采用更加隐蔽和间接的方式,对非西方国家实行政治与社会渗透,利用强势意识形态俘获非西方精英,扶植亲西方代理人,颠覆非西方国家的独立自主政权,最终将非西方国家重新成为其附庸。自冷战后期以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权颠覆,或称“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日益成为西方霸权国控制和摧毁非西方国家的主要手段。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这种双重压力,与非西方国家自身的“后发”特征相叠加,导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普遍存在三个矛盾:
一是强大的安全压力与有限的资源总量之间的矛盾。非西方国家经济起点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人力财力物力相对有限。在强大的外部安全压力下,如何既满足国防需求,又避免透支国力,不影响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必要积累和投入,是所有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必解题。一些非西方国家在军队和国防工业现代化取得成就后,未能兼顾发展和安全,而是任由“军工复合体”恶性膨胀,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最终积重难返。苏联模式的崩溃就是典型例证。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
二是借助外力与独立自主的矛盾。非西方国家既需要借助与第三方的战略合作制衡潜在的外部威胁,分担安全压力,又要避免这种合作损害本国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成为第三方的棋子和工具,从而损害自身的长远发展。越南在中国和苏联的大力支持下,战胜了法国殖民者、美国侵略者和南越傀儡政权,但越南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益倒向苏联阵营,甘做苏联在东南亚扩张势力范围的马前卒,最终也尝到了为第三方做代理人的苦果和教训。
三是对外开放与防范渗透的矛盾。任何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不能闭关自守、故步自封。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引入先发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有益的知识与文化。但西方国家的各类情报机构又必然会借着开放的大门,以扶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独立教会”“独立工会”和“独立媒体”为形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苏联和东欧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虽然有苏联模式水土不服的内因,但也有美国“和平演变”的外因。
相对于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国家建构等层面相对落后,在经济分工上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在政治上处于争取独立自主、摆脱西方控制与干涉的斗争状态,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处于相对弱势和非主流地位。这使得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是争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相对自主、独立和安全地位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和科技问题,而且是安全和稳定问题。
具体而言,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面临更大的外部安全压力:
其一,非西方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威胁。历史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是受迫的:正是为了回应和反抗西方列强的威胁、霸凌与侵略,非西方国家才开始建立现代化政治组织与社会汲取动员体系,实行各项改革,走向现代化道路。而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步后,西方列强甚至会变本加厉,试图将潜在的赶超者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二,非西方国家的政权安全时刻面临严峻的意识形态渗透压力。二战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国际体系的规范规则为之一新,西方列强无法像从前那样随意吞并、肢解和奴役一个主权国家。但西方列强转而采用更加隐蔽和间接的方式,对非西方国家实行政治与社会渗透,利用强势意识形态俘获非西方精英,扶植亲西方代理人,颠覆非西方国家的独立自主政权,最终将非西方国家重新成为其附庸。自冷战后期以来,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权颠覆,或称“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日益成为西方霸权国控制和摧毁非西方国家的主要手段。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这种双重压力,与非西方国家自身的“后发”特征相叠加,导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普遍存在三个矛盾:
一是强大的安全压力与有限的资源总量之间的矛盾。非西方国家经济起点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人力财力物力相对有限。在强大的外部安全压力下,如何既满足国防需求,又避免透支国力,不影响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必要积累和投入,是所有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必解题。一些非西方国家在军队和国防工业现代化取得成就后,未能兼顾发展和安全,而是任由“军工复合体”恶性膨胀,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最终积重难返。苏联模式的崩溃就是典型例证。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
二是借助外力与独立自主的矛盾。非西方国家既需要借助与第三方的战略合作制衡潜在的外部威胁,分担安全压力,又要避免这种合作损害本国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成为第三方的棋子和工具,从而损害自身的长远发展。越南在中国和苏联的大力支持下,战胜了法国殖民者、美国侵略者和南越傀儡政权,但越南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益倒向苏联阵营,甘做苏联在东南亚扩张势力范围的马前卒,最终也尝到了为第三方做代理人的苦果和教训。
三是对外开放与防范渗透的矛盾。任何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不能闭关自守、故步自封。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引入先发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有益的知识与文化。但西方国家的各类情报机构又必然会借着开放的大门,以扶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独立教会”“独立工会”和“独立媒体”为形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苏联和东欧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虽然有苏联模式水土不服的内因,但也有美国“和平演变”的外因。